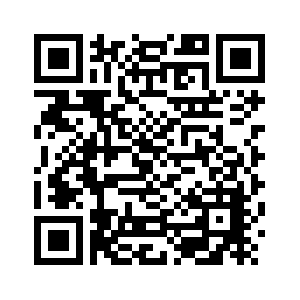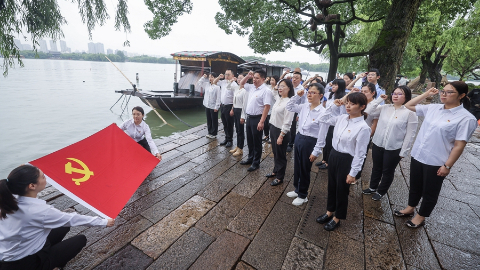电视剧《边水往事》《我的阿勒泰》《我是刑警》《西北岁月》《山花烂漫时》海报
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(中国剧单元)十部入围作品题材各有特色,但都透着一股鲜活的“青春语态”。
所谓“青春语态”,不是说演员年轻或故事只围绕青春展开,而是一种创作思维上的年轻态。它体现在对未知领域题材的开拓勇气,对传统叙事套路的勇敢打破,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持续探索。“青春语态”既助力中国电视剧抵达年轻观众,也为中国电视剧在多元娱乐的冲击中摸索出一条突围路径——让多元题材在创新表达中绽放异彩,让时代故事在青春视角下赢得共鸣。
题材开拓:触碰未知领域
在题材选择上,第30届白玉兰奖入围的中国电视剧展现出初生牛犊般的创作勇气:不局限于传统题材的窠臼,敢于触碰未知领域,拓宽电视剧的叙事疆域。
获得评委会大奖的《西北岁月》首次系统呈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历程,填补了重大革命题材的创作空白。窑洞、黄土地、石碾石磨等元素构成视觉基底,陕甘方言、民间习俗与耕作场景交织出浓郁的西北地域特色。该剧将历史叙事与地域文化相融合的创作手法,使红色题材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。
《边水往事》创造了一个名为“三边坡”的异质空间,热带丛林的潮湿气息几乎要穿透屏幕。这里并非我们熟悉的任何城市,乃法律与野性交织的灰色地带。剧中人物沈星在“跑边水”的过程中,既要应对各种危险场景,又要在人性善恶的夹缝中寻找生存之道。极端环境下的人性挣扎,超越了传统悬疑剧的框架,带有社会寓言色彩,让观众在感受冒险刺激的同时,感知主人公在困境中的底线坚守。
金融题材的《城中之城》令人耳目一新。该剧将镜头对准金融行业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领域,以银行为背景,通过两代金融人在利益与操守间的抉择,照见普遍的人性命题,为金融题材剧开辟了新的表达空间。该剧还将儒家伦理融入职场叙事,如凭借“白衬衫”等隐喻,让金融题材兼具时代性与文化深度。
《凡人歌》中三对都市夫妻的故事跳出“学区房”“婚外情”等套路,直面失业风险、职场压力、价值观冲突等危机,展现都市生活中个体在物质与精神夹缝中的挣扎。剧中沈磊一角的塑造颇具突破性,通过这个角色揭示了一些体制内青年面临的精神困境——稳定编制带来的安全感与职场进取心的矛盾,程序正义原则与人情社会的冲突。他在重重矛盾中的清醒自省与破局尝试,为都市青年在现实枷锁中寻找出口提供了充满希望的参照。
中国电视剧的“青春语态”,在题材上表现为对未知领域保持好奇与突破的勇气,在创作上展现出“破界”生长的生命力,对时代精神进行鲜活的回应。
叙事革新:重构故事逻辑
中国电视剧的“青春语态”不只体现在题材选择上,也在于叙事方式的革新。在面对一些传统类型剧时,创作者以开放心态重构故事逻辑,用崭新视角激活观众的情感共鸣。
《山花烂漫时》用全新视角重构了观众已经很熟悉的张桂梅校长的感人故事。剧集并未停留在单一人物传记的层面上,而是巧妙地将镜头对准“她与她们”的共生关系。张桂梅的信仰之光与山区少女的青春热血相互映照,形成独特的叙事张力。张桂梅“救一代人”的教育理想不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,而化作具体可感的青春叙事。剧中女孩们从认命到抗争的转变过程,让观众看到了信仰如何点燃生命。教育改变命运的命题通过青春群像得到生动诠释,使得主旋律题材更具感染力和时代气息。
年代剧《小巷人家》不依赖戏剧性事件推动情节,它让苏州小巷的日常细节成为叙事主体,以日常的温馨场景串联起时代变迁。几户人家的命运交织中,住房分配的焦虑、高考恢复的激动、个体经商的尝试,都通过邻里间的家长里短自然流露。剧中黄玲与宋莹的相处摒弃了狗血对立模式,构建起“小巷姐妹”的真实羁绊。苏州地域文化不是背景点缀,而已融入叙事内核,时代叙事因此兼具地域辨识度与生活穿透力,小巷成为人们观察社会变迁的棱镜。
获得评委会大奖的《我是刑警》脱离了刑侦剧常见的“神探”式个人英雄套路,以写实笔触还原刑侦工作的真实流程。叙事以时间线贯穿,经由不同时期的案件侦破,反映刑侦技术的演进。剧集将重案实录与主旋律主题结合,而大案是展现刑侦发展的载体,既保持纪实感,又紧扣职业精神的主题表达,为刑侦剧创作提供了新路径。
“青春语态”的叙事革新,本质是创作视角的自我更新。熟悉的类型因叙事革新而焕发新意,让观众在固有题材里看到了不一样的表达。
艺术手法:探索美学风格
当题材的边界被不断拓宽、叙事的逻辑被重新解构,电视剧的美学风格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实验浪潮——用更新颖、更新潮、更另类的形式传递价值内核。剧集由单纯的故事载体,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综合艺术品。
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的《我的阿勒泰》以“散文诗”风格探索影视美学新境。镜头如笔触,将北疆草原的雪山、花海、牧群化为流动的画面,4K影像捕捉草叶露珠与马鬃霜雪的质感,让自然成为叙事主体。叙事打破了强情节框架,以剧中人物李文秀的写作独白串联生活碎片——帮母亲要债的误会、转场途中的篝火、牧民婚礼的欢歌,像散文段落般随性舒展,却在细节中有情感涌动。慢节奏的镜头语言里,转场的祈祷仪式、宰羊待客的风俗等,都成为人与自然共生的图腾,“去爱,去生活”的主题如草原晨雾般轻柔弥漫,在治愈叙事中完成对心灵的温柔叩问。
《庆余年第二季》在艺术手法上呈现出鲜明的“网感”美学,与当代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契合。剧中大量运用了网络流行语和现代梗,比如主角范闲脱口而出的“YYDS”、叶轻眉字条上的《黑猫警长》歌词,打破了古装剧的时空壁垒,形成别具一格的时空错位幽默。范闲的“金手指”设定被赋予了现代价值观,他在封建体制中坚持平等理念的行为,实质是网络文化中“爽感”与理想主义的混合体。配角如王启年、范思辙以漫画式表演强化记忆点,这种处理源自网络文学对人物标签化的偏好,最终形成兼具深度与传播度的群像图谱。
《玫瑰的故事》的时尚美学风格独具匠心。镜头运用极具现代感,大量使用氛围镜头塑造人物,主人公黄亦玫回眸一笑的定格、办公室昂首挺胸的侧影,如时尚大片般考究。场景设计融合了艺术性与生活感——职场空间简约利落、家居环境温暖雅致、酒会场景华丽璀璨,构建出符合当代审美的都市图景。美术团队通过色彩搭配、光影调控,打造出兼具质感与格调的视觉体系,展现出对都市题材的前卫理解。
不重复的表现形式、不妥协的审美追求、对传统美学形式的突破与再造,是中国电视剧在艺术手法上的“青春语态”。创作者们以具有辨识度的风格探索,让影视艺术保持着与时代同频的敏锐触角、引领风尚的先锋姿态。
站在第30届的节点上,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见证的是这个评奖周期优秀中国电视剧的荣光,也是一个行业集体年轻化的蜕变。“青春语态”的本质是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,是以创新的勇气、敏锐的触角、突破的胆识让行业焕发朝气蓬勃的生命力。愿这份敢于打破、勇于探索的创作锐气,如同剧集中那些鲜活的角色,始终奔跑在寻找光的路上,让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激荡起更广泛的情感共鸣。(曾于里)